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当代艺术家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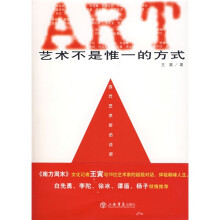
《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当代艺术家访谈录》完全有资格成为那些刚出道的文化记者的教科书。它将教会他们如何提问,如何从一大堆杂乱的印象中提炼出传神的细节嵌在报道里边,如何将一个高深的、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学者或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神采飞扬地、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普通读者,而且,我相信,它也会让那些书斋里的“专家型”读者感到大快朵颐,发出类似于“深得我心“的感叹。
这《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当代艺术家访谈录》完全有资格成为那些刚出道的文化记者的教科书。它将教会他们如何提问,如何从一大堆杂乱的印象中提炼出传神的细节嵌在报道里边,如何将一个高深的、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学者或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神采飞扬地、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普通读者,而且,我相信,它也会让那些书斋里的“专家型”读者感到大快朵颐.发出类似于“深得我心“的感叹。
王寅奠定他在诗歌界的江湖地位.差不多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他是《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采访过一大堆中外艺术界的不错人物,此前他是上海电视台的编导,参与制作过多集纪录片《长征》和有关老上海的专题片。
王寅刚到《南方周末》,便以一篇霍金观察记令大家震惊。在一次别说专访,就连抛出一个问题都不可能的“采访”中,他刀锋般犀利的现场观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采访台湾现代艺术家蒋勳的时候.王寅的提问显然是有备而来.蒋熏力也就很容易滔滔不绝。
王寅:有资料上说,你每年大概要作300次讲座,这个数字确切吗?……很多像今天这样公益性、普及性的讲座,我注意到下面有些学生在打嗑睡。
看到这种情况,你觉得还有必要和他们这样聊吗?蒋勳:美这个东西,她有时候就是刹那间显现一些东西给你,其实我不觉得美一定是一种知识。从你的讲座里面,他(她)会在只言片语里面得到一个什么启发,很难估量。……以前我们在故宫上课,没有窗户,在暗暗的房间里看幻灯片,其实也打瞌睡的,可是我常常觉得忽然惊醒的那一瞬间看到的东西会变成我后来限重要的东西。如果迷信地讲的话,你好像会在重要的东西到了的时候醒来。
一个实际的提问,被访者的回答却带有一些神秘的形而上的色彩。这是意外的收获。一个记者在采访中,意外越多,惊喜也越多。
王寅又问:“我看到张晓风在一篇文章中说你过着神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指你比较脱俗?”蒋勳的回答很精彩:“台北是个很混乱的城市,脏、乱,几平没有人觉得自己居住的环境好。我是住在淡水河的河口,当初我那个房子买得便宜得不得了,70万台币。12扇窗往外推就看见河口,我有时跟人家讲说也不输西湖的景。别人已经觉得像神仙了,你怎么可以过这样的日子?可是,有次,我看到唐伯虎50岁给自己写的诗,他说:“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日问眠。漫老海内传名字,谁信腰、司没酒钱?”大家都会觉得他过得像神仙,可是他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没有权,也没有财富,但是他可以过得像神仙。我想张晓风讲的神仙本质上就是自由。他常常羡慕我可以到处乱走,听说日本的米园大雪,我就带着川端康城的《雪国》去住上两天。”我们身边不大看得到这种为了米园的大雪带上川端康成的《雪国》专程飞一趟日本的浪漫怪人的,我们的媒体上宣扬得更多的倒是一些所谓成功人士为了招摇天下而实行的苦肉计式的折腾,和小资们的标榜另类实际已经很例牌的生活道具——法国闷片,村上春树的小说,布拉格的城市景观,诸如此类。但是我们仔细读完蒋勤的这篇专访,便可以知道.在我们是行头和饰品的东西,在他那儿大概已经修行得天然去雕饰.成为他生活中像空气一样自然的东西。即便造作,也造作得底气十足。
那些挑剔的被访者往往只对那些了解他的记者开口。碰到傻瓜记者的时候,他宁可把嘴巴闭上。某报曾经发过张某大明星接受记者采访的照片,照片上大明星的目光随着身子转向另边,完全背对记者。这个记者对如此不堪的待遇当然会感到怄气,但他也不妨想想,他的采访提纲里到底是些什么问题,他有没有做过充分的准备,他是不是动了脑筋,他是不是除了报纸杂志,不读任何别的东西。
中国有句说滥了的古话,“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句话用在采访上,倒是极其贴切的。提起被访者的兴致,是记者的一大学问,这就是为什么有的采访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有的采访原定半个小时,聊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还意犹未尽。
林怀民的采访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王寅的提问都是从他的观察中生发出来的。“我看见在彩排的时候,你一直在做笔记,只有过一次提示。我很好奇,你当时记的是什么?”“在谢幕的时候.我才看到演员是高矮不齐的,在演出的时候。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我注意到《竹梦》里个别片断舞蹈和音乐编织得不是很紧密,比如第二段的双人舞和三人舞。”“从风扇搬上舞台,就开始有了谐谑的成分,直到后的穿帮。”“台上的竹子是真的吗?”“《竹梦》用的是爱沙尼亚作曲家佩尔特的音乐。”有了前边的愉快的铺垫,当王寅问出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云门的下一个作品是什么?“时,林怀民的回答是一大段话(任何一个记者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林怀民很可能只是报一个剧目给他)两年前在印度,恒河岸边,我看见乳白色的烟从焚尸场升起,丧家的男子从头到脚裹着白的棉衣,胡子刮得非常干净,我想到我重病的父亲……于是有了《烟》。
……在台湾没有春天的感觉。这太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的场景:家族长老死去的时候,板栗树上的落花像雪片一样,狗被窒息死了。
后来在布拉格找音乐,我找了很久。音乐用的是许尼特克,我喜欢他的音乐喜欢得不得了,他是我严重的初恋。他的音乐很难弄,非常现代,又十分浪漫。他是犹太人,有德国血统,生长在俄罗斯。你看。多么复杂。布拉格路上的石板像有灵魂一样,安静得不得了。从旅馆的窗户可以看见卡夫卡墓地,绿色的树,绿色的苔藓,绿,全是绿色的,绿到让你昏倒。你可以想像那里冬天绿成什么样子。我回不到恒河了。
后来还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一块跳板,“有时,会忽然想起某个春天所听到的一个名字……”。
大树落下细细的白色的花,没有叶子的树想起它的春天。我用的是真的玫瑰花瓣,晒干了,是淡黄色的,在灯光下,是白的,很漂亮。现在,云门的门外就晒满了待用的玫瑰花瓣。
舞台上有一棵要几人才能环抱的大树,树上有20多片树叶。树下有一个小水池,一个小女孩死在里面,不穿衣服。水池里放的是真的水,是烧好的水,我们反复测试温度,要维持三分钟,不能太热,也不能还没有演完就冷了。你看,从出发点到终点,其实是不相干的。
如果是一家娱乐小报的记者去采访林怀民,用一大堆傻瓜问题令他瞠目结舌,他就绝对不会说出这么一段特别紧贴他的“身段”的话来:他不会说到印度与恒河,不会说到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不会说到许尼特克,不会说到布拉格的石板路和卡夫卡的墓地。不会说到普鲁斯特和《追忆逝水年华》,不会说到舞台上那棵有20多片叶子的树,更不会说那句几乎没头没脑的话:“你看,从出发到终点,其实是不相干的。“不能紧贴身段.便不能活画出他的本相。
当然,王寅完成漂亮的采访的一大前提便是,他自己也得有盎然的兴致。被访者越精彩,越合他的胃口,他的兴致越高,他甚至可以一次,两次,三次地和他们深谈,话题从核心弥散开去.直到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细节也成群结队地涌现出来。
人们已习惯于对诗人的文字存有某种迷信.但仅仅有漂亮的文字很难保证一个人可以成为好的记者。王寅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将他的文字锤炼得很漂亮,但他的采访有价值的部分,倒并不在于他的文体.而是他从被访者那里挖掘出的思想的金子、经验的白银。我相信,一个舞蹈工作者会从林怀民的专访中领会到很多深意.一个建筑师会从库尔哈斯和黑川纪章的专访中获得很多启发,一个热爱日本电影的读者会对那篇佐藤忠男的专访着迷,而我们普通读者,除了获得很多教益之外,还可以领略到一篇新闻报道可以好看到什么程度。
前不久,我在一《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当代艺术家访谈录》中看到一个法国人所做的对于塞尚的虚拟的采访,当我知道这篇对话是虚拟的以后.便把它放下了。我当然更愿意听塞尚的亲口说话,而不是一个自认为了解塞尚的人所做的“过度阐释”。王寅这《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当代艺术家访谈录》的大价值,便是对于当代众多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的原声呈现。
这《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当代艺术家访谈录》完全有资格成为那些刚出道的文化记者的教科书。它将教会他们如何提问,如何从一大堆杂乱的印象中提炼出传神的细节嵌在报道里边,如何将一个高深的、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学者或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神采飞扬地、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普通读者,而且,我相信,它也会让那些书斋里的“专家型”读者感到大快朵颐.发出类似于“深得我心“的感叹。
王寅奠定他在诗歌界的江湖地位.差不多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他是《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采访过一大堆中外艺术界的不错人物,此前他是上海电视台的编导,参与制作过多集纪录片《长征》和有关老上海的专题片。
王寅刚到《南方周末》,便以一篇霍金观察记令大家震惊。在一次别说专访,就连抛出一个问题都不可能的“采访”中,他刀锋般犀利的现场观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采访台湾现代艺术家蒋勳的时候.王寅的提问显然是有备而来.蒋熏力也就很容易滔滔不绝。
王寅:有资料上说,你每年大概要作300次讲座,这个数字确切吗?……很多像今天这样公益性、普及性的讲座,我注意到下面有些学生在打嗑睡。
看到这种情况,你觉得还有必要和他们这样聊吗?蒋勳:美这个东西,她有时候就是刹那间显现一些东西给你,其实我不觉得美一定是一种知识。从你的讲座里面,他(她)会在只言片语里面得到一个什么启发,很难估量。……以前我们在故宫上课,没有窗户,在暗暗的房间里看幻灯片,其实也打瞌睡的,可是我常常觉得忽然惊醒的那一瞬间看到的东西会变成我后来限重要的东西。如果迷信地讲的话,你好像会在重要的东西到了的时候醒来。
一个实际的提问,被访者的回答却带有一些神秘的形而上的色彩。这是意外的收获。一个记者在采访中,意外越多,惊喜也越多。
王寅又问:“我看到张晓风在一篇文章中说你过着神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指你比较脱俗?”蒋勳的回答很精彩:“台北是个很混乱的城市,脏、乱,几平没有人觉得自己居住的环境好。我是住在淡水河的河口,当初我那个房子买得便宜得不得了,70万台币。12扇窗往外推就看见河口,我有时跟人家讲说也不输西湖的景。别人已经觉得像神仙了,你怎么可以过这样的日子?可是,有次,我看到唐伯虎50岁给自己写的诗,他说:“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日问眠。漫老海内传名字,谁信腰、司没酒钱?”大家都会觉得他过得像神仙,可是他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没有权,也没有财富,但是他可以过得像神仙。我想张晓风讲的神仙本质上就是自由。他常常羡慕我可以到处乱走,听说日本的米园大雪,我就带着川端康城的《雪国》去住上两天。”我们身边不大看得到这种为了米园的大雪带上川端康成的《雪国》专程飞一趟日本的浪漫怪人的,我们的媒体上宣扬得更多的倒是一些所谓成功人士为了招摇天下而实行的苦肉计式的折腾,和小资们的标榜另类实际已经很例牌的生活道具——法国闷片,村上春树的小说,布拉格的城市景观,诸如此类。但是我们仔细读完蒋勤的这篇专访,便可以知道.在我们是行头和饰品的东西,在他那儿大概已经修行得天然去雕饰.成为他生活中像空气一样自然的东西。即便造作,也造作得底气十足。
那些挑剔的被访者往往只对那些了解他的记者开口。碰到傻瓜记者的时候,他宁可把嘴巴闭上。某报曾经发过张某大明星接受记者采访的照片,照片上大明星的目光随着身子转向另边,完全背对记者。这个记者对如此不堪的待遇当然会感到怄气,但他也不妨想想,他的采访提纲里到底是些什么问题,他有没有做过充分的准备,他是不是动了脑筋,他是不是除了报纸杂志,不读任何别的东西。
中国有句说滥了的古话,“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句话用在采访上,倒是极其贴切的。提起被访者的兴致,是记者的一大学问,这就是为什么有的采访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有的采访原定半个小时,聊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还意犹未尽。
林怀民的采访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王寅的提问都是从他的观察中生发出来的。“我看见在彩排的时候,你一直在做笔记,只有过一次提示。我很好奇,你当时记的是什么?”“在谢幕的时候.我才看到演员是高矮不齐的,在演出的时候。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我注意到《竹梦》里个别片断舞蹈和音乐编织得不是很紧密,比如第二段的双人舞和三人舞。”“从风扇搬上舞台,就开始有了谐谑的成分,直到后的穿帮。”“台上的竹子是真的吗?”“《竹梦》用的是爱沙尼亚作曲家佩尔特的音乐。”有了前边的愉快的铺垫,当王寅问出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云门的下一个作品是什么?“时,林怀民的回答是一大段话(任何一个记者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林怀民很可能只是报一个剧目给他)两年前在印度,恒河岸边,我看见乳白色的烟从焚尸场升起,丧家的男子从头到脚裹着白的棉衣,胡子刮得非常干净,我想到我重病的父亲……于是有了《烟》。
……在台湾没有春天的感觉。这太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的场景:家族长老死去的时候,板栗树上的落花像雪片一样,狗被窒息死了。
后来在布拉格找音乐,我找了很久。音乐用的是许尼特克,我喜欢他的音乐喜欢得不得了,他是我严重的初恋。他的音乐很难弄,非常现代,又十分浪漫。他是犹太人,有德国血统,生长在俄罗斯。你看。多么复杂。布拉格路上的石板像有灵魂一样,安静得不得了。从旅馆的窗户可以看见卡夫卡墓地,绿色的树,绿色的苔藓,绿,全是绿色的,绿到让你昏倒。你可以想像那里冬天绿成什么样子。我回不到恒河了。
后来还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一块跳板,“有时,会忽然想起某个春天所听到的一个名字……”。
大树落下细细的白色的花,没有叶子的树想起它的春天。我用的是真的玫瑰花瓣,晒干了,是淡黄色的,在灯光下,是白的,很漂亮。现在,云门的门外就晒满了待用的玫瑰花瓣。
舞台上有一棵要几人才能环抱的大树,树上有20多片树叶。树下有一个小水池,一个小女孩死在里面,不穿衣服。水池里放的是真的水,是烧好的水,我们反复测试温度,要维持三分钟,不能太热,也不能还没有演完就冷了。你看,从出发点到终点,其实是不相干的。
如果是一家娱乐小报的记者去采访林怀民,用一大堆傻瓜问题令他瞠目结舌,他就绝对不会说出这么一段特别紧贴他的“身段”的话来:他不会说到印度与恒河,不会说到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不会说到许尼特克,不会说到布拉格的石板路和卡夫卡的墓地。不会说到普鲁斯特和《追忆逝水年华》,不会说到舞台上那棵有20多片叶子的树,更不会说那句几乎没头没脑的话:“你看,从出发到终点,其实是不相干的。“不能紧贴身段.便不能活画出他的本相。
当然,王寅完成漂亮的采访的一大前提便是,他自己也得有盎然的兴致。被访者越精彩,越合他的胃口,他的兴致越高,他甚至可以一次,两次,三次地和他们深谈,话题从核心弥散开去.直到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细节也成群结队地涌现出来。
人们已习惯于对诗人的文字存有某种迷信.但仅仅有漂亮的文字很难保证一个人可以成为好的记者。王寅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将他的文字锤炼得很漂亮,但他的采访有价值的部分,倒并不在于他的文体.而是他从被访者那里挖掘出的思想的金子、经验的白银。我相信,一个舞蹈工作者会从林怀民的专访中领会到很多深意.一个建筑师会从库尔哈斯和黑川纪章的专访中获得很多启发,一个热爱日本电影的读者会对那篇佐藤忠男的专访着迷,而我们普通读者,除了获得很多教益之外,还可以领略到一篇新闻报道可以好看到什么程度。
前不久,我在一《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当代艺术家访谈录》中看到一个法国人所做的对于塞尚的虚拟的采访,当我知道这篇对话是虚拟的以后.便把它放下了。我当然更愿意听塞尚的亲口说话,而不是一个自认为了解塞尚的人所做的“过度阐释”。王寅这《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当代艺术家访谈录》的大价值,便是对于当代众多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的原声呈现。
比价列表
| 商家 | 评价 (0) | 折扣 | 价格 |
 | 暂无 | 京东缺货N个月 |  24小时内更新 |


 缺书网
缺书网 扫码进群
扫码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