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域纪程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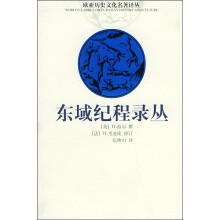
目 录内容简介
《东域纪程录丛》两卷于1866年出版。这是亨利·裕尔爵士为哈克路特学会编纂的第二部著作。几年前(1863年)裕尔曾译注过乔达努斯修士的《东方奇特事物》。这两部著作很长时间已绝版。《东域纪程录丛》的副本间或出现在书商的目录表上,索价奇高。长期以来它一直是所有从事古代和中世纪远东研究的人的便览手册,对于这样一本书,我无需再加以赞美。大家都承认,对于所有感兴趣于中国、中亚历史地理,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历史地理的人们,《东域纪程录丛》都是必备的研究指南。这本书问世时,它几乎囊括了迄至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尽管这位博学的编纂者谦逊地使用了《中世纪中国见闻汇编》这一副标题。1866年以来,由于新地域的发现和人们在迄今未被充分研究的国家所做的旅行,科学特别是地理学获得迅速的发展。裕尔本人在他1871年初次印行的巨著《马可·波罗游记》的新版本中,已加入了大量新材料,但未对《东域纪程录丛》进行补充。所以,有必要出版新的《东域纪程录丛》,将所有最新资料搜罗进去。我曾是《马可·波罗游记》第三版的编订者,大家认为我有特殊的资格来完成这项新的任务。我的故交、博学的哈克路特学会主席马卡姆爵士,请我担当修订《东域纪程录丛》的重任。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借此机会表达我对裕尔其人的敬慕之意和对这位早已闻其大名的地理学家的钦佩之情。
在这里可以重述我在《马可·波罗游记》第三版前言中说过的话:“对于亨利·裕尔爵士的注释,我几乎未做任何删除,只是作了很少的变动。只有在最近的资料证明他有错的情况下,我才这样做。我对裕尔的注释做了补充,希望这些补充被证明是有用的新材料。”在修订《东域纪程录丛》时,我尽可能坚持这些原则,但是,除了附加众多的注释外,预论中增加了以最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关于中亚的新的一章,还有少量补充性注释。大家认为这是必要的。关于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知识一章的开端部分已全部改写。新增加的材料已使这部著作的篇幅变得很大,所以觉得应将它印成四卷,而不是两卷[1]。
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前言中,我们提到一些著作,除此之外,还应提到奥瑞尔·斯坦因爵士有关他在中亚所做旅行及其发现的论述,我的同僚和朋友沙畹教授论述西突厥的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聪慧睿智的年轻学者伯希和教授为我补充的众多价值极高的注释。我还可以提到其他许多著作,但这些著作将在注释或附在第四卷末尾的书目中看到。
关于伊本·白图泰,像约翰·布尼安(John Bunyan)的拉丁文译本一样,“我的译本转自阿拉伯文”;但不是从李所依据的略本,而是像德弗里麦里(M.M.Defrémery)和桑圭奈蒂(Sanguinetti)法译本一样依据未删节的游记。虽然译文版本借用,但注解没有借用;而且我坚信,对于这位充满好奇心的旅行家,我的评注会提供一些新的见解。
在本书征引的其他作家中,自负、聒噪但又颇为诚实的约翰·德·马黎诺利是最引人注目的。他的作品偶尔被埃默森·坦南特爵士引用。对于埃默森·坦南特爵士,很少事物能逃脱他如炬的目光。如果不是埃默森·泰南特注意到他,我想马黎诺利在英国几乎是不会为人所知的。
本书所收入的每一位作者,在讲述他们的故事前,都将在适当的位置介绍其背景经历,所以这里不需要对他们逐个多费笔墨。
对文中出现的重复,我无需辩解。在一本汇编而非选集中,重复不可避免。但在注释中有时也出现重复,则将是可怕的。对这种情况,我请求宽宥。我的住处离印刷厂很远,客观环境要求我先将前面的稿件交付印刷厂,而后面的部分在数月后才告完成,这样我无法对整个著作进行通贯的修改。
一些好心的朋友不惮其烦向我提供参考书,或解答与本书相关的问题。我对他们表示热诚谢意;但这里我将只提及梅杰君和马卡姆君的名字;承蒙二位好心,他们还依次检读了排印中的二校印样。
在这里可以重述我在《马可·波罗游记》第三版前言中说过的话:“对于亨利·裕尔爵士的注释,我几乎未做任何删除,只是作了很少的变动。只有在最近的资料证明他有错的情况下,我才这样做。我对裕尔的注释做了补充,希望这些补充被证明是有用的新材料。”在修订《东域纪程录丛》时,我尽可能坚持这些原则,但是,除了附加众多的注释外,预论中增加了以最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关于中亚的新的一章,还有少量补充性注释。大家认为这是必要的。关于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知识一章的开端部分已全部改写。新增加的材料已使这部著作的篇幅变得很大,所以觉得应将它印成四卷,而不是两卷[1]。
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前言中,我们提到一些著作,除此之外,还应提到奥瑞尔·斯坦因爵士有关他在中亚所做旅行及其发现的论述,我的同僚和朋友沙畹教授论述西突厥的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聪慧睿智的年轻学者伯希和教授为我补充的众多价值极高的注释。我还可以提到其他许多著作,但这些著作将在注释或附在第四卷末尾的书目中看到。
关于伊本·白图泰,像约翰·布尼安(John Bunyan)的拉丁文译本一样,“我的译本转自阿拉伯文”;但不是从李所依据的略本,而是像德弗里麦里(M.M.Defrémery)和桑圭奈蒂(Sanguinetti)法译本一样依据未删节的游记。虽然译文版本借用,但注解没有借用;而且我坚信,对于这位充满好奇心的旅行家,我的评注会提供一些新的见解。
在本书征引的其他作家中,自负、聒噪但又颇为诚实的约翰·德·马黎诺利是最引人注目的。他的作品偶尔被埃默森·坦南特爵士引用。对于埃默森·坦南特爵士,很少事物能逃脱他如炬的目光。如果不是埃默森·泰南特注意到他,我想马黎诺利在英国几乎是不会为人所知的。
本书所收入的每一位作者,在讲述他们的故事前,都将在适当的位置介绍其背景经历,所以这里不需要对他们逐个多费笔墨。
对文中出现的重复,我无需辩解。在一本汇编而非选集中,重复不可避免。但在注释中有时也出现重复,则将是可怕的。对这种情况,我请求宽宥。我的住处离印刷厂很远,客观环境要求我先将前面的稿件交付印刷厂,而后面的部分在数月后才告完成,这样我无法对整个著作进行通贯的修改。
一些好心的朋友不惮其烦向我提供参考书,或解答与本书相关的问题。我对他们表示热诚谢意;但这里我将只提及梅杰君和马卡姆君的名字;承蒙二位好心,他们还依次检读了排印中的二校印样。
比价列表





 缺书网
缺书网 扫码进群
扫码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