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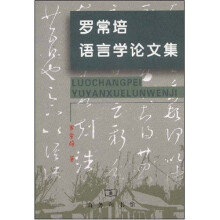
目 录内容简介
罗常培先生字莘田,号恬庵,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8月9日生于北京一个满族平民家庭。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因父亲刚去世,不得不负起全家生活重担,一边读书,一边在众议院做速记,半工半读直至毕业,又转入哲学系读了两年。1921年离北大后,在京津两地教中学,并代理过校长。1926年,到西安任西北大学国学专修科主任兼教授,讲授音韵学。次年回京。1926年至1928年先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1929年到刚成立于广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专力研究中国音韵学和汉语方言。1934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兼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辗转到长沙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任教。次年学校迁云南,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他随校入滇。1940年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兼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1944年赴美国讲学,1948年回国,继续在北大教书,并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他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被任命为所长。他还被任命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1949年),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1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年,1954年改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5年)。1954年和1958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51年起患高血压症,仍长期带病辛勤工作,终于不治,1958年12月13日逝世,刚满59岁。
罗先生在学术界工作约30年,主要是在研究所专力研究和在大学任教;任教也从来没有停止研究工作,而是将研究所得充实教材或开设新课。例如《汉语音韵学导论》一书,就是在许多所大学教音韵学的讲义,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历时20余年,前后修订8次,才正式出版的。研究、教书互相促进。他多方面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新局面,教出许多方面语言研究专门人才,不愧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他的业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音韵学研究。音韵学发展到20世纪初,上古音的声部和中古音的声类、韵类的分合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积累了经过研究整理的大量资料。如果要更进一步,就必须有新方法、新工具、新材料。罗先生适逢其时。他充分研究了前人各家音韵学著作,包括国外汉学家这方面的著作,全面掌握历代音韵资料。在这基础上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现代语音学方法,引用方言和梵汉、汉藏等对音材料,对音韵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关于古代某些声韵母读音和音类分合的独到见解。这方面的论文,如《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1930年)、《知彻澄娘音值考》(1930年),等等,都是力作名篇。常被引用。另一方面,对音韵学中的某些术语,主要是等韵中的术语,做了使人容易理解的音理解释,如《释内外转》(1933年)、《释重轻》(1932年)等。罗先生的工作使传统音韵学从“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的状态上升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他还对前人某些较为生僻的音韵著作,用序跋的形式加以评介,给以音韵史中的适当位置。为了填补传统音韵学从上古音到切韵音中间的一大段空白,他对汉魏南北朝的韵部进行了全面研究,另外,沿切韵音往下延伸,研究近代音,写了《(中原音韵>声类考》等论文。这就跟现代音相贯通了。
二、方言研究。罗先生研究汉语方言是跟研究汉语语音史密切相关的。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专著《厦门音系》和论文《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前者用历史的语言系统驾驭现代复杂的方音,后者用六朝韵文中所反映的方言特点帮助考证并构拟历史语音。1940年出版《临川音系》一书,把临川语音同切韵音和现代北京语音作了比较,对某些“特殊词汇”作了语源学的探索。1933年出版了《唐五代西北方言》,利用了梵汉、汉藏对音,在方法上是创新,是用现代语音学方法去考证汉语古代方音的典范之作。他还调查了在方言分类上很有价值的徽州方言,写过几篇介绍这个方言特点的文章,个别材料用作他某些著作的例证。广大官话(大北方话)内部差异的调查,那时还没引起方言研究者的兴趣。罗先生独具只眼,抗战期间在昆明写了《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发表。十余年后许多性质和名称都类似的书接连出现,为推广普通话起了重要作用。罗先生这篇文章实开其先河。他还对西汉杨雄《方言》以下,直至清末各家的方言著述,作出总结式述评。罗先生方言研究的特色是贯穿古今,多作比较,不只是平面描写。
三、民族语言研究。他从汉语方言研究转入民族语言研究是在抗战时期的云南。这里民族语言众多,语言学者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引自他《语言学在云南》)。他以身作则,鼓励并带领学生进行调查,曾三次为此去大理,平日在昆明也找发音人记录。他调查了民家(白)语、纳西语、俅(独龙)语、怒语、景颇语、傈僳语、摆夷(傣)语。发表了《莲山摆夷语初探》(与邢庆兰合著)、《贡山俅语初探》(中文、英文)、《贡山怒语初探叙论》等。有些材料用作他别的著作的例子,如《普通语音学纲要》(与王均合著)就引用不少;《语言与文化》中也不难发现。更重要的是,一些青年学者在他的带动下逐渐成为民族语研究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民族语言调查,他们起了骨干和种子作用。
四、借鉴域外。罗先生研究音韵史,早在20年代末就注意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为学习汉语用罗马字母拼汉字的材料,写了《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长篇论文(1930年,十余年后又写了补篇)。后来这工作扩大到传教士之外的许多国外与汉语研究有关的著作,逐一单篇介绍。又在大学开设《域外中国声韵学论著述评》课程,并编成讲义印发。域外中国声韵学重要著作中当首推瑞典高本汉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作于1915—1926年)。当年中央研究院打破不译书成例,特委托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三位,经多年努力把此书由法文译成中文,并改正其中错案,补充某些材料。这个译本1940年出版以来,对我国语言学界的影响至今未衰。罗先生除了在《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1935年)着重介绍高氏此书,还发表了专篇介绍。罗先生顺着研究耶稣会士的汉语拼音往下走,从另一方向扩大到对我国拼音字母源流的研究。这既是学术专题,也为配合当时的推行国语运动。他研究了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制定前各家各派为标注字音或拼写口语的字母,陆续发表,后总成《国音字母演进史》一书(1934年)。50年代中期,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中,这书应需要改名为《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重印。
五、铺起一条中国语言学新的路基。语言学所以列为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和产生语言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早在《临川音系》的叙论里,罗先生就论述了临川话和客赣话的历史关系。后来这叙论抽出加以修订,单独发表,题为《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进一步阐明民族迁徙和语言演变的关系。40年代他在云南,结合语言调查,注意搜集有“父子连名制”这一民族文化特征的材料,连大理荒郊野外的墓碑也未放过。他数次发表有关“父子连名制”的文章。后来总成一篇分为三纲六项十三目的长文《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这篇文章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云南西部人数多、分布广的民家(白族)应属藏缅族;二是以大理为中心的古南诏国(约8世纪至10世纪)的建国者是有父子连名制文化特征的藏缅族中的彝族和仍有这特征遗迹的白族的祖先,而不是没有这特征的非藏缅族称为“白夷”或“摆夷”的傣族。罗先生另一拓展语言学的力作是《语言与文化》一书。这书写定于北京解放的炮声中,而框架构建和资料积累由来已久。他用大量语言事实,论证语言与人类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关系,并“自信这本小书对中国语言学新路把路基初步铺起来了”。这书40年后重印,被推许为“我国第一部文化语言学开创性著作”。
六、音韵学的普及工作。在这方面,罗先生主要从两项工作使深奥难懂的音韵学去影响社会:一是把音韵学延伸到文艺领域,解决其中某些问题,显示音韵学并非一门孤立的“绝学”,而是与文艺相通,对文艺有用的学问。他初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就写了《音韵学与戏剧》(1935年)、《旧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1936年)等从课堂通向剧场的文章。能体现他这方面业绩的,是《北平俗曲百种摘韵》一书。他用“丝贯绳牵”法归纳100种北平俗曲押韵而成。1942年在重庆出版后,当地《新华日报》写专篇书评介绍,称它“就内容说,称得起是一本通俗的科学著作,而所附的字汇,又可以实际帮助诗人们用来合辙押韵。”这本书解放后曾两次重印(改名为《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可见受到社会重视。罗先生普及音韵学知识另一方法是直接写些浅近易懂的有关音韵学的文章。30年代,就有《音韵学研究法》一文(1934年)。十年以后,又写了《音韵学不是绝学》(1944年)。这两篇文章的十年中间,他写了一系列音韵学通俗性专题文章,如《从“四声”说到“九声”》(1939年)、《四声五声六声八声皆为周氏所发现》(1941年)、《什么叫双声叠韵》(1942年)、《汉语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1942年)、《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1944年)等等。他本来打算把这些文章集结为《恬庵说音》一书,跟《中国音韵学导论》相辅而行。因出国讲学,无暇整理作罢。
罗先生的一生业绩联系着我国语言学发展的许多方面。诚如魏建功先生所说:“他称得起是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是继往开来出力多的人。”罗先生自己也说过:“我们的工作应为后人铺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他逝世40多年来,主要是近20多年来,我国语言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正是他生前的愿望。
罗先生在学术界工作约30年,主要是在研究所专力研究和在大学任教;任教也从来没有停止研究工作,而是将研究所得充实教材或开设新课。例如《汉语音韵学导论》一书,就是在许多所大学教音韵学的讲义,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历时20余年,前后修订8次,才正式出版的。研究、教书互相促进。他多方面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新局面,教出许多方面语言研究专门人才,不愧为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他的业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音韵学研究。音韵学发展到20世纪初,上古音的声部和中古音的声类、韵类的分合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积累了经过研究整理的大量资料。如果要更进一步,就必须有新方法、新工具、新材料。罗先生适逢其时。他充分研究了前人各家音韵学著作,包括国外汉学家这方面的著作,全面掌握历代音韵资料。在这基础上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现代语音学方法,引用方言和梵汉、汉藏等对音材料,对音韵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关于古代某些声韵母读音和音类分合的独到见解。这方面的论文,如《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1930年)、《知彻澄娘音值考》(1930年),等等,都是力作名篇。常被引用。另一方面,对音韵学中的某些术语,主要是等韵中的术语,做了使人容易理解的音理解释,如《释内外转》(1933年)、《释重轻》(1932年)等。罗先生的工作使传统音韵学从“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的状态上升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他还对前人某些较为生僻的音韵著作,用序跋的形式加以评介,给以音韵史中的适当位置。为了填补传统音韵学从上古音到切韵音中间的一大段空白,他对汉魏南北朝的韵部进行了全面研究,另外,沿切韵音往下延伸,研究近代音,写了《(中原音韵>声类考》等论文。这就跟现代音相贯通了。
二、方言研究。罗先生研究汉语方言是跟研究汉语语音史密切相关的。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专著《厦门音系》和论文《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前者用历史的语言系统驾驭现代复杂的方音,后者用六朝韵文中所反映的方言特点帮助考证并构拟历史语音。1940年出版《临川音系》一书,把临川语音同切韵音和现代北京语音作了比较,对某些“特殊词汇”作了语源学的探索。1933年出版了《唐五代西北方言》,利用了梵汉、汉藏对音,在方法上是创新,是用现代语音学方法去考证汉语古代方音的典范之作。他还调查了在方言分类上很有价值的徽州方言,写过几篇介绍这个方言特点的文章,个别材料用作他某些著作的例证。广大官话(大北方话)内部差异的调查,那时还没引起方言研究者的兴趣。罗先生独具只眼,抗战期间在昆明写了《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发表。十余年后许多性质和名称都类似的书接连出现,为推广普通话起了重要作用。罗先生这篇文章实开其先河。他还对西汉杨雄《方言》以下,直至清末各家的方言著述,作出总结式述评。罗先生方言研究的特色是贯穿古今,多作比较,不只是平面描写。
三、民族语言研究。他从汉语方言研究转入民族语言研究是在抗战时期的云南。这里民族语言众多,语言学者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引自他《语言学在云南》)。他以身作则,鼓励并带领学生进行调查,曾三次为此去大理,平日在昆明也找发音人记录。他调查了民家(白)语、纳西语、俅(独龙)语、怒语、景颇语、傈僳语、摆夷(傣)语。发表了《莲山摆夷语初探》(与邢庆兰合著)、《贡山俅语初探》(中文、英文)、《贡山怒语初探叙论》等。有些材料用作他别的著作的例子,如《普通语音学纲要》(与王均合著)就引用不少;《语言与文化》中也不难发现。更重要的是,一些青年学者在他的带动下逐渐成为民族语研究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民族语言调查,他们起了骨干和种子作用。
四、借鉴域外。罗先生研究音韵史,早在20年代末就注意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为学习汉语用罗马字母拼汉字的材料,写了《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长篇论文(1930年,十余年后又写了补篇)。后来这工作扩大到传教士之外的许多国外与汉语研究有关的著作,逐一单篇介绍。又在大学开设《域外中国声韵学论著述评》课程,并编成讲义印发。域外中国声韵学重要著作中当首推瑞典高本汉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作于1915—1926年)。当年中央研究院打破不译书成例,特委托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三位,经多年努力把此书由法文译成中文,并改正其中错案,补充某些材料。这个译本1940年出版以来,对我国语言学界的影响至今未衰。罗先生除了在《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1935年)着重介绍高氏此书,还发表了专篇介绍。罗先生顺着研究耶稣会士的汉语拼音往下走,从另一方向扩大到对我国拼音字母源流的研究。这既是学术专题,也为配合当时的推行国语运动。他研究了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制定前各家各派为标注字音或拼写口语的字母,陆续发表,后总成《国音字母演进史》一书(1934年)。50年代中期,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中,这书应需要改名为《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重印。
五、铺起一条中国语言学新的路基。语言学所以列为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和产生语言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早在《临川音系》的叙论里,罗先生就论述了临川话和客赣话的历史关系。后来这叙论抽出加以修订,单独发表,题为《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进一步阐明民族迁徙和语言演变的关系。40年代他在云南,结合语言调查,注意搜集有“父子连名制”这一民族文化特征的材料,连大理荒郊野外的墓碑也未放过。他数次发表有关“父子连名制”的文章。后来总成一篇分为三纲六项十三目的长文《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这篇文章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云南西部人数多、分布广的民家(白族)应属藏缅族;二是以大理为中心的古南诏国(约8世纪至10世纪)的建国者是有父子连名制文化特征的藏缅族中的彝族和仍有这特征遗迹的白族的祖先,而不是没有这特征的非藏缅族称为“白夷”或“摆夷”的傣族。罗先生另一拓展语言学的力作是《语言与文化》一书。这书写定于北京解放的炮声中,而框架构建和资料积累由来已久。他用大量语言事实,论证语言与人类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关系,并“自信这本小书对中国语言学新路把路基初步铺起来了”。这书40年后重印,被推许为“我国第一部文化语言学开创性著作”。
六、音韵学的普及工作。在这方面,罗先生主要从两项工作使深奥难懂的音韵学去影响社会:一是把音韵学延伸到文艺领域,解决其中某些问题,显示音韵学并非一门孤立的“绝学”,而是与文艺相通,对文艺有用的学问。他初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就写了《音韵学与戏剧》(1935年)、《旧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1936年)等从课堂通向剧场的文章。能体现他这方面业绩的,是《北平俗曲百种摘韵》一书。他用“丝贯绳牵”法归纳100种北平俗曲押韵而成。1942年在重庆出版后,当地《新华日报》写专篇书评介绍,称它“就内容说,称得起是一本通俗的科学著作,而所附的字汇,又可以实际帮助诗人们用来合辙押韵。”这本书解放后曾两次重印(改名为《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可见受到社会重视。罗先生普及音韵学知识另一方法是直接写些浅近易懂的有关音韵学的文章。30年代,就有《音韵学研究法》一文(1934年)。十年以后,又写了《音韵学不是绝学》(1944年)。这两篇文章的十年中间,他写了一系列音韵学通俗性专题文章,如《从“四声”说到“九声”》(1939年)、《四声五声六声八声皆为周氏所发现》(1941年)、《什么叫双声叠韵》(1942年)、《汉语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1942年)、《反切的方法及其应用》(1944年)等等。他本来打算把这些文章集结为《恬庵说音》一书,跟《中国音韵学导论》相辅而行。因出国讲学,无暇整理作罢。
罗先生的一生业绩联系着我国语言学发展的许多方面。诚如魏建功先生所说:“他称得起是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是继往开来出力多的人。”罗先生自己也说过:“我们的工作应为后人铺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他逝世40多年来,主要是近20多年来,我国语言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正是他生前的愿望。
比价列表价格走势






 缺书网
缺书网 扫码进群
扫码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