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的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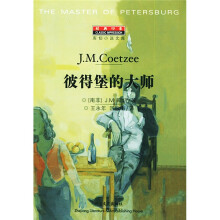
《彼得堡的大师》在另一个向度上,库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人和其他作品的人物也邀请到 1869年的彼得堡,让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地下室”、“火”等属于陀思安耶夫斯基话语的场景里,参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中去。小说中,库切多采用现在进行时,并用他(he)来叙述,形成作品中的共时性。情节在共时性的作用下,使人物的自由行动处在一种关键时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库切让自己的主人公承受特殊的精神折磨,以此逼迫主人公把达到极度紧张的自我意识讲出来。正如巴赫金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是些思想家式的人物:具有伟大而尚未解决的思想的小人物。那么,在《彼得堡的大师》中,库切创造了思想的陀思安耶夫斯基。这样,不仅是陀思安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具有开放的、鲜活的他人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拥有完全独立的声音,发出价值十足的议论,与作者形成多重的平等的对话关系。如果说陀思安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复调的,那么《彼得堡的大师》是复调的复调。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以及那些有着特殊意味的场景
经过库切鬼斧神工般的裁剪和微调,呈现得扑朔迷离、亦真亦幻,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折射出丰富的寓意。
1971年,库切回到南非,后在开普敦大学任教。其间,他深入研究俄罗斯文学,做过陀思安耶夫斯基专题。库切是喜欢实验的,也许在研究中,遗世独立的陀思安耶夫斯基还引起了他的共鸣,一种慢慢相借的感情使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进了小说,当然用的是他小说家的生花妙笔,来表达他对另一位作家的敬意。在对人的命题的探险历程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中,库切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是同行与对话者。库切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所经历的革命的俄国生活有着异形同构的特质。所以,库切孜孜不倦地叙述种族隔离这一特殊境况下人的状态,并引发对普遍的人性的探究,他的声调是悲哀的。正如《等待野蛮人》书名所昭示的,即便野蛮人不存在,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把他发明和捏造出来。在库切笔下,人的内心深处总潜藏着魔鬼,不失时机地要把它投射到某种便利的替罪羊身上。同样的命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魔鬼有时就寄生在无原则的恐怖主义中,表达了他对俄国革命的反省。在《彼得堡的大师》中,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和错综复杂的文本互涉,无论是库切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一个政治的隐喻,一种政治的哲学。
然而,《彼得堡的大师》是澄澈的。也许这种澄澈来自库切对文字有力的节制和叙述上的冷静。但《彼得堡的大师》是动情的,也许这种动情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深深的敬意。
经过库切鬼斧神工般的裁剪和微调,呈现得扑朔迷离、亦真亦幻,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折射出丰富的寓意。
1971年,库切回到南非,后在开普敦大学任教。其间,他深入研究俄罗斯文学,做过陀思安耶夫斯基专题。库切是喜欢实验的,也许在研究中,遗世独立的陀思安耶夫斯基还引起了他的共鸣,一种慢慢相借的感情使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进了小说,当然用的是他小说家的生花妙笔,来表达他对另一位作家的敬意。在对人的命题的探险历程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中,库切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是同行与对话者。库切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所经历的革命的俄国生活有着异形同构的特质。所以,库切孜孜不倦地叙述种族隔离这一特殊境况下人的状态,并引发对普遍的人性的探究,他的声调是悲哀的。正如《等待野蛮人》书名所昭示的,即便野蛮人不存在,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把他发明和捏造出来。在库切笔下,人的内心深处总潜藏着魔鬼,不失时机地要把它投射到某种便利的替罪羊身上。同样的命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魔鬼有时就寄生在无原则的恐怖主义中,表达了他对俄国革命的反省。在《彼得堡的大师》中,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和错综复杂的文本互涉,无论是库切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一个政治的隐喻,一种政治的哲学。
然而,《彼得堡的大师》是澄澈的。也许这种澄澈来自库切对文字有力的节制和叙述上的冷静。但《彼得堡的大师》是动情的,也许这种动情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深深的敬意。
比价列表







 缺书网
缺书网 扫码进群
扫码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