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馆:黑色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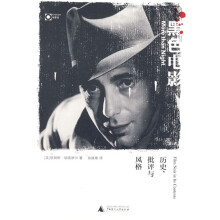
《电影馆:黑色电影》提供了对黑色电影的原创性研究方法,既生动又广博,同时还有新的影片信息和对数十部影片带有启发意义的评论,这其中包括经典之作《双重赔偿》《马耳他之鹰》《第三个人》《来自过去》,“新黑色电影”《唐人街》《低俗小说》《蓝衣魔鬼》,以及 21世纪的黑色电影《穆赫兰道》《罪恶之城》《杀戮赌场》等。纳雷摩尔对黑色电影的探讨基于以下几个面向:作为批评主义的术语,作为艺术中现代主义的表达,作为好莱坞1940、1950年代审查制度和政治的征候,作为一种市场策略,作为一种不断演进的风格,作为关于种族和民族的电影,作为一个通过各种信息技术得以传播的概念。
《黑色电影》还是一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著作,除了电影和电视,笔力所及,还带来有关现代文学、美术、流行文化的有益见地。
《黑色电影》中文版推荐序:《黑色电影:历史、形式与风格》和詹姆斯?纳雷摩尔
乔纳森?罗森鲍姆
一
“中国人并不认为过去的事物有多重要,”大概十年前,张曼玉在接受一本法国杂志采访时说,“不管那是电影、遗产,甚至衣服或家具。在亚洲,没有任何东西会被保存,恋旧被认为是愚蠢和反常的。”(Les Inrockuptibles,1999年12月1日)
饶有趣味的是,至少对于我而言,这一说法解释了为何那么多重要的中国电影关注历史的发现,它们代表了打捞某段失落过往的各种尝试。在此,我仅列十二部我喜爱的中国电影,它们都显现出上述特征: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侯孝贤的《悲情城市》(1989)和《戏梦人生》(1993),王家卫的《阿飞正传》(1990)和《花样年华》(2000),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关锦鹏的《阮玲玉》(1992),田壮壮的《蓝风筝》(1993),李少红的《红粉》(1994),贾樟柯的《站台》(2000)、《三峡好人》(2006)和《二十四城记》(2008)。恰如我一篇作于2001年的文章的标题——描述的是《阮玲玉》——这有点像是“在流沙中建筑历史 ”(Building History in Quicksand)。甚至其他许多我所钟爱的中国电影,即便它们沉潜于当下,在当下的所有现代性中观照这个当下,例如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1996)、陈可辛的《甜蜜蜜》(1996)、贾樟柯的《世界》(2004),也许都可被视为历史地看待当下的野心之作。
张曼玉的说法也可用于描绘很多美国人的偏失,尽管它较不适用于对于詹姆斯?纳雷摩尔和我所成长的地方:美国南方。自从在南北战争(1861—1865)——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家所承受的具备创伤性的文化危机(部分是因为它结束了奴隶制),有两部著名的美国电影都对此做了描绘,它们是《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和《飘》(Gone With the Wind,1939)——中战败,南方人便经常对那个被假想存在于战前的神话般的黄金时代抱有一种渴望的怀旧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争辩,怀念一个想象的过去也是一种贬低历史的方式。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值钱的资本主义工具,让某些产品得以贩卖和再次贩卖,对于一个渴望历史又深深怀疑历史的当下来说,更是如此。
黑色电影与过去之间便存在着能够反映这种矛盾心态的复杂而暧昧的关系,就我所知,纳雷摩尔是迄今为止出色地描述这一现象并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他开始于一个悖论:今天的美国,几乎任何一个步入音像店的人都知道“黑色电影”是什么而当初那些美国观众见到这类好莱坞经典——全都制作于1940和1950年代——时,他们并没听说或知道这个术语。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今日对黑色电影的喜好乃是出于对一个从未存在的过去的怀念——至少,那个过去并不以我们现在所理解它的方式而存在着。
《黑色电影》还是一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著作,除了电影和电视,笔力所及,还带来有关现代文学、美术、流行文化的有益见地。
《黑色电影》中文版推荐序:《黑色电影:历史、形式与风格》和詹姆斯?纳雷摩尔
乔纳森?罗森鲍姆
一
“中国人并不认为过去的事物有多重要,”大概十年前,张曼玉在接受一本法国杂志采访时说,“不管那是电影、遗产,甚至衣服或家具。在亚洲,没有任何东西会被保存,恋旧被认为是愚蠢和反常的。”(Les Inrockuptibles,1999年12月1日)
饶有趣味的是,至少对于我而言,这一说法解释了为何那么多重要的中国电影关注历史的发现,它们代表了打捞某段失落过往的各种尝试。在此,我仅列十二部我喜爱的中国电影,它们都显现出上述特征: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侯孝贤的《悲情城市》(1989)和《戏梦人生》(1993),王家卫的《阿飞正传》(1990)和《花样年华》(2000),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关锦鹏的《阮玲玉》(1992),田壮壮的《蓝风筝》(1993),李少红的《红粉》(1994),贾樟柯的《站台》(2000)、《三峡好人》(2006)和《二十四城记》(2008)。恰如我一篇作于2001年的文章的标题——描述的是《阮玲玉》——这有点像是“在流沙中建筑历史 ”(Building History in Quicksand)。甚至其他许多我所钟爱的中国电影,即便它们沉潜于当下,在当下的所有现代性中观照这个当下,例如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1996)、陈可辛的《甜蜜蜜》(1996)、贾樟柯的《世界》(2004),也许都可被视为历史地看待当下的野心之作。
张曼玉的说法也可用于描绘很多美国人的偏失,尽管它较不适用于对于詹姆斯?纳雷摩尔和我所成长的地方:美国南方。自从在南北战争(1861—1865)——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家所承受的具备创伤性的文化危机(部分是因为它结束了奴隶制),有两部著名的美国电影都对此做了描绘,它们是《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和《飘》(Gone With the Wind,1939)——中战败,南方人便经常对那个被假想存在于战前的神话般的黄金时代抱有一种渴望的怀旧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争辩,怀念一个想象的过去也是一种贬低历史的方式。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值钱的资本主义工具,让某些产品得以贩卖和再次贩卖,对于一个渴望历史又深深怀疑历史的当下来说,更是如此。
黑色电影与过去之间便存在着能够反映这种矛盾心态的复杂而暧昧的关系,就我所知,纳雷摩尔是迄今为止出色地描述这一现象并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他开始于一个悖论:今天的美国,几乎任何一个步入音像店的人都知道“黑色电影”是什么而当初那些美国观众见到这类好莱坞经典——全都制作于1940和1950年代——时,他们并没听说或知道这个术语。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今日对黑色电影的喜好乃是出于对一个从未存在的过去的怀念——至少,那个过去并不以我们现在所理解它的方式而存在着。
比价列表价格走势








 缺书网
缺书网 扫码进群
扫码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