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嫁
作者:绕梁三日 著
出版: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9
页数:288
定价:29.80 元
ISBN-13:9787511228116
ISBN-10:7511228119
去豆瓣看看 节选一 霍时英站在城门口,和她爹隔了两丈远,一身灰突突的短襟布衣,脚上的布鞋一只前面戳出一个洞来。 霍将军骑着高头大马,鲜衣铠甲,眯着眼睛看着她半晌:“卢龙寨守三日行吗?” 霍时英舔舔干裂的嘴唇,西北的日头烈,她也眯着眼看她爹,她爹霍真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纨绔,在西北边关混了二十年终于混成了一个老兵痞,他是她的上司,而且还是她爹。 霍时英垂下眼皮,用没露脚趾头的那只鞋踢了踢脚下的灰土:“羌人的大军只要开到这城底下,别说三天了,三个时辰都守不住。你就给我留了两千的兵,站城头上刚好填满,羌人这次来了二十万,他们就是叠着人梯一个个上来踩都能把我们踩死了。”霍时英这话说得闷突突的,一点都没有人家跑路她留下垫背的激愤,她蔫头耷脑闷闷的几句话,霍将军听着就有点不舒服了。 霍将军手里的马缰绳稍稍紧了一点,那匹马原地踏出几步,他手里的马鞭烦躁地一挥:“那就不打了?也不守了?你这能守三天,大军就能多撤出五百里去,出了甘宁道,到了凉州府,那才算有点胜算,你这里要是守不住羌人的大军破了卢龙寨,一出嘉定关,他们的骑兵一泻而下,占了甘宁道劫了粮道这仗还打什么打?” 霍时英仰着头,不紧不慢地说:“我七天前就给你送过信了,嘉定关有多少兵?七天还撤不完?你们从七天前开始撤这会儿至少应该到凉州府了。”末了她又疲惫地加了一句:“真不行!” 秋日干燥的西北风里,霍时英顶着一张灰扑扑的脸,额头和脸颊上灰尘和着汗水,汗被风吹干了,留下几道黑黑的痕迹,一把枯草一样的头发用根布条绑着,两人马上马下地互相看着。 霍将军从霍时英的脸一直看到她露着脚趾头的鞋,来回扫了她几遍,最终眼底一抹狠厉之色闪过,抬了抬马鞭指着她道:“守不住也要守,少一个时辰我亲手把你的头砍下来。” 将军留下这句话,扬起马蹄绝尘而去,身后跟着他的一群亲卫,一群彪悍的大马奔驰而去,扬起一阵灰尘呛了霍时英一鼻子灰。 霍将军的马队跑得没影了,霍时英像个遇上灾年的农民窝囊地蹲在自家的地头上一样,泄气地往城门口一蹲。 捡了根草棍,霍时英蹲在城门口的地上左一道右一道地画了起来,半盏茶的工夫,前面又传来一阵马蹄声,她抬眼望去,她爹猩红的斗篷在风里一扬一扬地又飘了回来。 霍将军在霍时英的面前刹住马势,灰尘中父女俩马上马下地对望着。 霍真四十多岁了,还是很英俊的一张脸,他没像现下流行的那样是个男人都蓄着一把美须,白净的一张脸,边关二十年的岁月也没破坏他脸上的美感。这个中年美男子定定地看了霍时英半晌最后忽然贱兮兮地笑着说:“ 时英,最后一仗了,打完了爹带你回家。” 霍将军说完看了她脚下杂乱无章的一堆涂鸦一眼,然后忽然就笑了,笑得有点狡猾,笑完了,又看了霍时英一眼,再次马蹄飞扬潇洒地跑了。 扬起一堆比刚才还要大的灰尘,霍时英裹在弥漫的尘土里,眼前闪过一堆堆雕梁画栋,金粉佳人,“家?”她两岁多时来到边关整整二十年就回去过一次,那年她十二岁,给她奶奶请安,在屋外面跪了三个时辰,那次还正赶上她一个姐姐出嫁,她和那个姐姐一句话没说对,又被她奶奶罚跪了半天,最后还是他爹得到消息,进屋踢翻了她奶奶房里的一个花瓶,她爹跟她奶奶干上了,这才放了她。 可那个家也真漂亮啊,那么大的宅院,一进套一进的院子,边角旮旯都摸不到灰,连仆人都干干净净,一个个整齐漂亮的,还有她二哥的手可真白啊,还有早上白定桥边早市的味道真好闻,雾蒙蒙的早上,空气里飘着阵阵水汽。霍时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马上一口灰吸进嘴里,狠狠地呛了她一口。 一边咳嗽着一边站起来拍拍屁股往回走,霍时英进了城门迎面和六条大汉碰上,是她爹的十八个亲卫中的六个,打头的还是她师傅,她迎上去问:“师傅您这不跟将军走,在这干吗呐?” 牵着马站在最前面的汉子,抱拳行了一礼,半张脸埋在胡子里,那剩下的半张也瘫着,瓮声瓮气地说:“禀都尉,将军让我们留下来做你的护卫。” 霍时英走上前拍拍汉子手里牵的马:“我爹还行,‘飞龙’都舍得给我留下了,这是让我逃跑的时候用呐。” “将军说了,卢龙寨守不住三天哪怕少一个时辰就把飞龙砍了,再绑了你去见他。”汉子瓮声瓮气地接着说。 霍时英摸着马头的手僵在半空,她张着嘴看着汉子,想说什么,没说出来,最后把手拐了个弯朝着他们挥了挥:“行了行了,那你们就到军营里自己找个地方窝着去吧,等羌人一破城你们就砍了飞龙,绑了我跑吧。 ” 霍时英说完懒得再搭理他们自己往城里走去,走出十几步后面一阵滚雷一样的铿锵之声跟着就来了:“将军还说了,此乃国难,卢龙寨一役至关生死,拜托都尉了!” 霍时英往前走不了了,一回身笔直射向那几个人的目光锋利如刀,可人家那几位也没搭理她牵着马扭身走了,估计真是到军营里找个地方窝着去了。 霍时英知道她这个师傅脑子有点憨,可这憨蠢到这个地步也实在让人生气,这种事是能站在城门口吼的吗?这乱了军心是个多大的事。 霍时英气得直哆嗦,看着边上巡逻的两队兵走过来了,最后还是窝囊地甩甩袖子走了。
……
绕梁三日:射手座、O型、短发女孩。自由生长,向阳,好水。喜爱童话,嗜读各色爱情文本,从《海的女儿》到《红楼梦》,从亦舒到简·奥斯汀,相信这世界确有爱情存在,心存美好总会迎来幸福。看过一些风景,细水长流地写着自己的爱情故事。
三年前为了平定西疆,他迎娶了雍州兵马总督的女儿为皇后,但他却在有生之年遇见了霍时英,这个世间独一无二的女子,这个大燕朝唯一的女将军。她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关注了她整整二十年,从他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见她的名字被母后和长姐提起,他就在想一个两岁的女娃娃被带到边关是多么的神奇。 十多年后他再次在战报上看见她的名字,霍时英三个字瞬间在他的眼前勾勒出一幅苍凉的画卷,大漠飞烟,骏马奔驰,金盔卫甲,立马横刀的英武女子,荒凉而充满生命的张力,残酷而柔情,如此强烈的冲击。只因为一个名字就给了他如此多的幻想,怦然心动。 后来他悄悄地给了她很多的机会,她的名字一次次地出现在战报上,一次次的功绩,鲜血淋漓,杀戮决断,他无数次幻想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子。 后来他知道了她的小字叫安生。安生?他如何能给她安生,他已经没有资格了,他大婚的时候挑起皇后盖头的那一刻,心里在隐隐地后悔,直到最后真正地见到她,那一刻滔天的悔意能盖天灭地。 没有人知道,他关注了她整整二十年。
比价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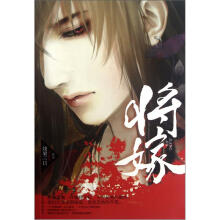
 缺书网
缺书网 扫码进群
扫码进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