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莎墓园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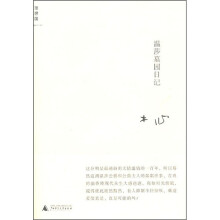
至今我还执著儿时看戏的经验,每到终场,那值台的便衣男子,一手拎过原是道具的披彩高背椅,咚地摆定台口正中,另一手甩出长型木牌,斜竖在椅上——
“明日请早。”
他这几个动作,利落得近乎潇洒,他不要看戏,只等终场,好去洗澡喝酒赌博困觉了——我仰望木牌,如梦而难醒,江南古镇的旧家子弟,不作兴夜夜上戏院,尤其是自己年纪这么小。
再说那年代的故乡,没有经常营业的戏院,要候“班子”开码头开来了,才贴出红绿油光纸的海报,一时全镇骚然,先涌到埠口的帮岸上,看那几条装满巨大箱笼的船,戏子呢,就是爬动在船首船艄的男男女女,穿着与常人无异,或者更见褴褛些,灰头土脸没有半点杨贵妃赵子龙的影子,奇怪的是戏子们在船上栗栗六六,都不向岸上看,无论岸上多少人,不看,径自烧饭,喂奶,坐在舷边洗脚,同伙间也少说笑,默默地吃饭了。岸上的人没有谁敢与船上招呼,万一走来个喊话的,大家就不看船上而看岸上的那个了。
混绿得泛白的小运河慢慢流,汆过瓜皮烂草野狗的尸体,水面飘来一股土腥气,镇梢的铁匠鎚声丁丁……寂寞古镇人把看戏当作大事,日夜两场,日场武戏多,名角排在夜场,私采行头簇崭新,票价当然高得多。预先买好戏票,兴匆匆吃过夜饭,各自穿戴打扮起来,勿要忘记带电筒,女眷们临走还解解手,照照镜子,终于全家笑逐颜开地出门了,走的小街是石板路,年久失修,不时在脚底磔咯作响,桥是圆洞桥,也石砌的,上去还好,下来当心打滑,街灯已用电灯,昏黄的光下,各路看客营营然往戏院的方向汇集。
“看戏呀?”
“嗳看戏!”
古镇哪里有戏院,是借用佛门伽蓝,偌大的破庙,“密印寺”,荒凉幽邃,长年狐鼠蝙蝠所据,忽然锣鼓喧天灯火辉煌,叫卖各式小吃的摊子凑成色香味十足的夜市,就是不看戏,也都来此逗留一番。
戏呢,毋须谈,以后或者谈。散戏,众人嗡嗡然推背接踵而出寺门,年纪轻的跨圮墙跳断垣格外便捷,霎时满街身影笑语像是还有什么事情好做,像是一个方向走的,却越走越岔渐渐寥落,寒风扑面,石板的磔咯声在夜静中显得很响,电筒的光束忽前忽后,上桥了,豆腐作坊的高烟囱顶着一湾新月,下面河水黑得像深潭,沿岸民房接瓦连檐偶有二三明窗,等候看戏者的归返——跟前的一切怎能与戏中的一切相比,本来也未必看出眼前的人没意趣,见过戏中的人了,就嫌眼前的人实在太没意趣,而“眼前的人”,尤其就是指自己,被“戏”抛弃,绝望于成为戏中人。
我执著的儿时看戏的经验宁是散场后的忧悒,自从投身于都市之后,各类各国的戏应接不暇,剧终在悠扬的送客曲中缓步走到人潮汹汹的大街上,心中仍是那个始于童年的阴沉感喟——“还是活在戏中好”,即使是全然悲惨了的戏。
“分身”“化身”似乎是我的一种欲望,与“自恋”成为相反的趋极。明知不宜作演员,我便以写小说来满足“分身欲”“化身欲”——某编辑先生于刊出《两个小人在打架》后,再度约稿时声称:“我们知道您曾经担任过中学国文教师……”某编辑女士览及《完美的女友》之类,访谈中提起:“看到了为您缝制丝质衬衫的女雕刻家等您从前的伴侣,可否请您谈谈您的诸多‘情障’。”某青年读者来信问:“从本书看,你幼年家境很好,教养是不错的,后来怎会一事无成的呢?”《芳芳NO.4》引起女读者的义忿,其中有位姑娘力主“芳芳是个好女孩”,所以“你怎么就这样看待她”——我没有在中学教过国文。也没有作过石油工程师与女雕刻家旧情复叙。福音医院是有的,美国孟医生对于我是陌生人。我从一个男人身上取了“芳芳”的模特儿,那音乐家的原型却是个女的;情况既然颠倒,也即是本来就没有这回事——当时我并未按实回复编者读者,怕会被认为我讳避抵赖,认为我不够朋友。
如果要够朋友一下,便得拈动三个名词,梦、生活、艺术,此三者被反复烹调得十分油腻,只可分别抉取其根本性质——不自主、半自主、全自主——我偏爱以“第一人称”营造小说(也通用于散文和诗),就在乎对待那些“我”,能全然由我做主。
“……袋子是假的,袋子里的东西是真的。当袋子是真的时,袋子里的东西是假的了。”(一则笔记)
再多解释就难免要失礼。还是顾左右而续叙往事吧——古镇春来,买卖蚕种筹开桑行的热潮,年年引起盛大的集市,俗称“轧蚕花”,庙会敬奉的主神名叫“蚕花娘娘”,不见得就是指螺祖。那娘娘有个独生的“蚕花太子”,是喜欢看戏的,所以在一切的闹忙中,扣人心弦者还是借此机会大家有得戏看,旷地上搭起巍然木阁,张幔蒙帘,悬皤插旗,蚕花太子用小轿抬来摆在好的位置上,咚咚惶惶,人山人海,全本《狸猫换太子》,日光射在戏台边,亮相起覇之际,凤冠霞帔蟒袍绣甲,被春暖的太阳照得格外耀眼,脸膛也更如泥做粉捏般的红白分明,管弦锣鼓齐作努力,唱到要紧关头,乌云乍起,阵雨欲来,大风刮得台上的缎片彩带乱飘乱飘,那花旦捧着螺钿圆盒瑟瑟价抖水袖,那老生执棍顿足:“天哪,天……哪……”一声声慷慨悲凉,整个田野的上空乌云密布,众人就是不散,都要看到底,盒子里的究竟是太子、是狸猫……
这种“草台戏”即所谓“社戏”,浙江上八府往往开演在祠堂里,如果现成的戏台临河,便围泊了许多乌篷船,启篷仰观,观罢荡橹而去。下三府的敬神献戏,贪图看客多多,向木行借来长条毛板,面对戏台架作马蹄形的层座,外边便是大片大片嫩绿的秧田,辣黄的油菜花发着浓香,紫云英锦毯也似的一直铺到河岸,然而日日见惯的平凡景致,哪里抵得过戏台上的行头和情节,灿烂曲折惊心动魄,即使太子总归假的,即使狸猫总归假的,而其中总归有真的什么在——我的童年,或多或少还可见残剩下来的“民间社会”,之后半个世纪不到就进入了“现代”,商品极权和政令极权两者必居其一的“现代”,在普遍受控制的单层面社会中,即使当演员,也总归身不由己,是故还是写写小说(其实属于叙事性散文),用“第一人称”聊慰“分身”“化身”的欲望,宽解对天然“本身”的厌恶。至此,童年看戏散场后小街磔咯作响的石板,桥堍豆腐工场高烟囱上的新月,也被装在前面所说的那种袋子里而不再怨尤了。
“明日请早。”
他这几个动作,利落得近乎潇洒,他不要看戏,只等终场,好去洗澡喝酒赌博困觉了——我仰望木牌,如梦而难醒,江南古镇的旧家子弟,不作兴夜夜上戏院,尤其是自己年纪这么小。
再说那年代的故乡,没有经常营业的戏院,要候“班子”开码头开来了,才贴出红绿油光纸的海报,一时全镇骚然,先涌到埠口的帮岸上,看那几条装满巨大箱笼的船,戏子呢,就是爬动在船首船艄的男男女女,穿着与常人无异,或者更见褴褛些,灰头土脸没有半点杨贵妃赵子龙的影子,奇怪的是戏子们在船上栗栗六六,都不向岸上看,无论岸上多少人,不看,径自烧饭,喂奶,坐在舷边洗脚,同伙间也少说笑,默默地吃饭了。岸上的人没有谁敢与船上招呼,万一走来个喊话的,大家就不看船上而看岸上的那个了。
混绿得泛白的小运河慢慢流,汆过瓜皮烂草野狗的尸体,水面飘来一股土腥气,镇梢的铁匠鎚声丁丁……寂寞古镇人把看戏当作大事,日夜两场,日场武戏多,名角排在夜场,私采行头簇崭新,票价当然高得多。预先买好戏票,兴匆匆吃过夜饭,各自穿戴打扮起来,勿要忘记带电筒,女眷们临走还解解手,照照镜子,终于全家笑逐颜开地出门了,走的小街是石板路,年久失修,不时在脚底磔咯作响,桥是圆洞桥,也石砌的,上去还好,下来当心打滑,街灯已用电灯,昏黄的光下,各路看客营营然往戏院的方向汇集。
“看戏呀?”
“嗳看戏!”
古镇哪里有戏院,是借用佛门伽蓝,偌大的破庙,“密印寺”,荒凉幽邃,长年狐鼠蝙蝠所据,忽然锣鼓喧天灯火辉煌,叫卖各式小吃的摊子凑成色香味十足的夜市,就是不看戏,也都来此逗留一番。
戏呢,毋须谈,以后或者谈。散戏,众人嗡嗡然推背接踵而出寺门,年纪轻的跨圮墙跳断垣格外便捷,霎时满街身影笑语像是还有什么事情好做,像是一个方向走的,却越走越岔渐渐寥落,寒风扑面,石板的磔咯声在夜静中显得很响,电筒的光束忽前忽后,上桥了,豆腐作坊的高烟囱顶着一湾新月,下面河水黑得像深潭,沿岸民房接瓦连檐偶有二三明窗,等候看戏者的归返——跟前的一切怎能与戏中的一切相比,本来也未必看出眼前的人没意趣,见过戏中的人了,就嫌眼前的人实在太没意趣,而“眼前的人”,尤其就是指自己,被“戏”抛弃,绝望于成为戏中人。
我执著的儿时看戏的经验宁是散场后的忧悒,自从投身于都市之后,各类各国的戏应接不暇,剧终在悠扬的送客曲中缓步走到人潮汹汹的大街上,心中仍是那个始于童年的阴沉感喟——“还是活在戏中好”,即使是全然悲惨了的戏。
“分身”“化身”似乎是我的一种欲望,与“自恋”成为相反的趋极。明知不宜作演员,我便以写小说来满足“分身欲”“化身欲”——某编辑先生于刊出《两个小人在打架》后,再度约稿时声称:“我们知道您曾经担任过中学国文教师……”某编辑女士览及《完美的女友》之类,访谈中提起:“看到了为您缝制丝质衬衫的女雕刻家等您从前的伴侣,可否请您谈谈您的诸多‘情障’。”某青年读者来信问:“从本书看,你幼年家境很好,教养是不错的,后来怎会一事无成的呢?”《芳芳NO.4》引起女读者的义忿,其中有位姑娘力主“芳芳是个好女孩”,所以“你怎么就这样看待她”——我没有在中学教过国文。也没有作过石油工程师与女雕刻家旧情复叙。福音医院是有的,美国孟医生对于我是陌生人。我从一个男人身上取了“芳芳”的模特儿,那音乐家的原型却是个女的;情况既然颠倒,也即是本来就没有这回事——当时我并未按实回复编者读者,怕会被认为我讳避抵赖,认为我不够朋友。
如果要够朋友一下,便得拈动三个名词,梦、生活、艺术,此三者被反复烹调得十分油腻,只可分别抉取其根本性质——不自主、半自主、全自主——我偏爱以“第一人称”营造小说(也通用于散文和诗),就在乎对待那些“我”,能全然由我做主。
“……袋子是假的,袋子里的东西是真的。当袋子是真的时,袋子里的东西是假的了。”(一则笔记)
再多解释就难免要失礼。还是顾左右而续叙往事吧——古镇春来,买卖蚕种筹开桑行的热潮,年年引起盛大的集市,俗称“轧蚕花”,庙会敬奉的主神名叫“蚕花娘娘”,不见得就是指螺祖。那娘娘有个独生的“蚕花太子”,是喜欢看戏的,所以在一切的闹忙中,扣人心弦者还是借此机会大家有得戏看,旷地上搭起巍然木阁,张幔蒙帘,悬皤插旗,蚕花太子用小轿抬来摆在好的位置上,咚咚惶惶,人山人海,全本《狸猫换太子》,日光射在戏台边,亮相起覇之际,凤冠霞帔蟒袍绣甲,被春暖的太阳照得格外耀眼,脸膛也更如泥做粉捏般的红白分明,管弦锣鼓齐作努力,唱到要紧关头,乌云乍起,阵雨欲来,大风刮得台上的缎片彩带乱飘乱飘,那花旦捧着螺钿圆盒瑟瑟价抖水袖,那老生执棍顿足:“天哪,天……哪……”一声声慷慨悲凉,整个田野的上空乌云密布,众人就是不散,都要看到底,盒子里的究竟是太子、是狸猫……
这种“草台戏”即所谓“社戏”,浙江上八府往往开演在祠堂里,如果现成的戏台临河,便围泊了许多乌篷船,启篷仰观,观罢荡橹而去。下三府的敬神献戏,贪图看客多多,向木行借来长条毛板,面对戏台架作马蹄形的层座,外边便是大片大片嫩绿的秧田,辣黄的油菜花发着浓香,紫云英锦毯也似的一直铺到河岸,然而日日见惯的平凡景致,哪里抵得过戏台上的行头和情节,灿烂曲折惊心动魄,即使太子总归假的,即使狸猫总归假的,而其中总归有真的什么在——我的童年,或多或少还可见残剩下来的“民间社会”,之后半个世纪不到就进入了“现代”,商品极权和政令极权两者必居其一的“现代”,在普遍受控制的单层面社会中,即使当演员,也总归身不由己,是故还是写写小说(其实属于叙事性散文),用“第一人称”聊慰“分身”“化身”的欲望,宽解对天然“本身”的厌恶。至此,童年看戏散场后小街磔咯作响的石板,桥堍豆腐工场高烟囱上的新月,也被装在前面所说的那种袋子里而不再怨尤了。
比价列表







 缺书网
缺书网 扫码进群
扫码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