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中国(套装共4册)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江城》 《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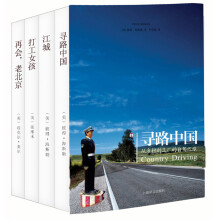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重要的变化。《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江城》
《江城》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2001年,也就是《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如今,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一百年来欧洲移民到美国总人数的三倍。
新一代农民工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外出的动机也更多是因为对城市机会的追求,而不是受农村贫困所迫。
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你的命运。
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着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我也更能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
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在工厂里你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姑娘: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带来的艰难或机遇。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一个个体。
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绝大多数外国媒体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许多写中国农民工的书也并不真实。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多,或许失去也多。
《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
北京,充满活力的中国之都,变化是不变的主题。
对中国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自北京建城以来,她就是吸引外来人口、商人、学者和探险者的魅力之地,其中也包括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这副“棋盘”的遗址仍留在北京城内,六十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和曼哈顿区差不多大,那些叫做胡同的狭窄巷子也依然存在。胡同之于北京,就如河道之于威尼斯。几个世纪以来,胡同一直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即使现在的巷子还不到以前的八分之一。
北京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城市。1962年,一名外国记者将这里定义为“史上大的乡村”。尽管这里有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机场,近一百家星巴克和一条覆盖到城市核心之外的新的地铁系统,但在某些北京人的眼中,它仍是一个乡村。
过去十年,就像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首都那样,北京这个大乡村走向了国际。穿过天安门广场,一百多公里外的长城标志着这个城市宽广的界限。或许它的改变可以用这个小插曲来说明:
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写:再现古都。
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
对于路人而言,这两个口号都可以是正确的,北京又处在八百年一次的再建与重生的循环之中。被改掉的横幅在几小时内就被扯了下来,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北京人不需要读它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他们每天都身处其中。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重要的变化。《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江城》
《江城》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2001年,也就是《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定义他们的流动生活。“在家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如今,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一百年来欧洲移民到美国总人数的三倍。
新一代农民工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外出的动机也更多是因为对城市机会的追求,而不是受农村贫困所迫。
是自尊,而不是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你的命运。
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着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我也更能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
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在工厂里你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姑娘: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工作带来的艰难或机遇。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一个个体。
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绝大多数外国媒体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许多写中国农民工的书也并不真实。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多,或许失去也多。
《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
北京,充满活力的中国之都,变化是不变的主题。
对中国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自北京建城以来,她就是吸引外来人口、商人、学者和探险者的魅力之地,其中也包括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这副“棋盘”的遗址仍留在北京城内,六十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和曼哈顿区差不多大,那些叫做胡同的狭窄巷子也依然存在。胡同之于北京,就如河道之于威尼斯。几个世纪以来,胡同一直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即使现在的巷子还不到以前的八分之一。
北京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城市。1962年,一名外国记者将这里定义为“史上大的乡村”。尽管这里有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机场,近一百家星巴克和一条覆盖到城市核心之外的新的地铁系统,但在某些北京人的眼中,它仍是一个乡村。
过去十年,就像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首都那样,北京这个大乡村走向了国际。穿过天安门广场,一百多公里外的长城标志着这个城市宽广的界限。或许它的改变可以用这个小插曲来说明:
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写:再现古都。
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
对于路人而言,这两个口号都可以是正确的,北京又处在八百年一次的再建与重生的循环之中。被改掉的横幅在几小时内就被扯了下来,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北京人不需要读它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他们每天都身处其中。
比价列表价格走势




 缺书网
缺书网 扫码进群
扫码进群